- 收藏
- 加入书签
跨世纪之争: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研究综述及发展新探索
摘要: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是否存在,引起了语言学、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讨论,至今仍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文通过对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提出的实验方法、实验数据、研究范式等进行综合分析、研判,认为要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拓展研究策略,并提出宏观问题微观解决的指导思想,认为应该从脑的神经系统入手来研究人类语言形成机制,用语言的本质回答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是否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关键期假说;神经科学;第二语言
1 引言
关键期(critical period简称CP)概念来源于生物学研究现象,是指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影响能起最大作用的时期。关键期中,在环境的影响下,个体高效习得某种行为特别容易,发展特别迅速。[1]D.Spalding在1872年通过实验验证:小鸡出生后的三天内被蒙住眼睛,以此剥夺它的视觉经验,过了适当的时间把布揭开时,小鸡首先会看见实验者的手,这时它就会跟随看手来移动,也就是说小鸡会跟随看见的第一个移动物行走,这个移动物体被小鸡认为是“妈妈”;如果错过这个时间点比如第四天才把蒙布揭开,那么小鸡看见移动的手就会惊慌地逃走。O.Heinroth(1910)和Lorenz(1935)在其他动物身上都发现了类似现象,Lorenz把这种在一定时间内,即关键期具有认母的这种现象称为印刻现象(imprinting),错过关键期很难再认母。研究者们进行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证明了生物学中关键期的存在。[2]
2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形成过程
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通过对婴幼儿的认真观察,用观察法归纳出儿童发展的九种关键期,其中语言关键期是0-6岁。[3]
“大脑的可塑性假说”(Brain Plasticity Hypothesis)提出者Penfield & Roberts通过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了语言与大脑的紧密联系,并在1959年指出:10岁以下的儿童更容易掌握语言。首次把生物范畴的关键期概念借鉴到人类语言习得领域。
著名神经心理学家Lenneberg在1967年出版的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语言的生物学基础》书中他总结出:人类2岁之前大脑尚未完全发育,习得语言的效率不高;青春期之后人类大脑会出现所谓的大脑偏侧化(brain lateralization)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说大脑最外层皮质分成的左右两个半球在青春期前都有语言习得功能,青春期后大脑的语言功能偏向了左半球,语言习得效率也会下降,显然只有在2岁到青春期这个年龄段,人类学习语言效率最高,这就是著名的“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简称CPH)。这一理论的发表,激发了语言学、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多领域学术界学者的热烈讨论,并将研究的视野扩大至第二语言的重要性时间段,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到目前为止,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Second language critical period)假说是否成立仍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
3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支持者观点
支持者认为,关键期(CPH)的存在可以通过语音、句法和语义的学习来证明,并利用传统心理学的语言行为实验与问卷调查,结合认知神经科学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断层扫描(PET)、核磁功能成像(fMRI)等技术,实现多维度技术手段共同参与来说服不同意见者
Johnson和Newport(1989,1991)与Johnson(1992)测试了母语为朝鲜语,第二语言学习年龄为3-39岁的被试,测试结论是:青春期前句法合理性判断的成绩与到达年龄相关显著,青春期之后成绩低且不稳定;7岁时测试成绩出现转折点;3-7岁组的成绩和母语组没有显著差异,其他年龄段被试的成绩显著低于母语组;青春期前获得第二语言的被试成绩显著高于青春期后获得第二语言的被试成绩。
Wartenburger等(2003)在研究二语习得中年龄和熟练程度的相关关系的过程中,使用了磁共振造影技术(FMRI)对双语被试者进行语法和语义判断时大脑皮质的活动测试。测试结论表明: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小的被试在加工自己的母语和第二语言时,大脑活动基本一致;第二语言习得年龄大的被试在进行二语语法加工时,与母语语法相比,参与加工的脑区更为广泛。这从神经学的角度证实了关键期的存在。
Long(1990)深入探讨了关键期如何影响儿童的二语习惯,他汇集和整理出众多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归纳,发现6岁以前的儿童在接触第二语言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口音特征,但是12岁以上的儿童的非母语发音就通常伴随着一定的口音特征。经过若干年深入研究,Long(2007)又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由来支持二语习得存在关键期的合理性:第一,全球的孩子们几乎都是在儿童时期学习语言;第二,在儿童时期,任何时间开始学习第二语言都能完成语言学习任务;第三,第二语言习得效率降低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成熟发生的现象。
4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反对者观点
反对者通过实验数据等多种研究范式反驳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成立这一观点。
第二语言语种是英语,母语语种是西班牙语的被试参加了Birdsong和Bialystok&Kenji Hakuta(1999)主持的与语音学习相关的研究实验,实验研究呈现的事实是被试年龄过了青春期一样可以有效习得第二语言,且成绩不输母语,从而证明了关键期假说不成立。与此同时语法学习领域的研究在Bialystok和Kenji Hakuta(1999)两位著名教授的领导下也取得了突破,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示在语法习得过程中关键期假说不成立。Birdsong教授再接再厉与Molis教授合作(2001),他们在语言各个要素的学习过程中都验证了青春期后也能很好学习第二语言,而且成绩与第一语言不相上下,也说明语言习得关键期不存在。以上三个实验结论都否定了关键期假说存在的观点。[18]
Snow C.E.和Hoefnagel-Hhle(1978)在自然环境过程中做了为期13个月的学习语言测试研究,他们选择了42名母语为英语的荷兰语学习者为被试,年龄从3岁到成年不等。实验研究事实是年龄小的实验组成员和年龄大的实验组成员展现的成绩都非常令人满意,在第二语言学习速度方面有力地推翻了关键期假说。
根据Flege(1999)的研究结果,当人们初次接触两种语言时,他们对目标语的语法掌握情况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没有随着人们的年龄增长而变化,也没有随着“关键期假说”的内容的更新而变化。因此得出结论:人们的语法掌握情况的改变主要取决于对目标语的掌握情况的是否持续提高。
国内学术界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了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辩论。首次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语种验证二语关键期假说是否成立是柴省三领导的课题组实现的[4],他们选择了209名被调查者,这些被调查者是来自16个不同国家在中国的留学生,测试范围包括汉字的词汇、语义、语法、语音等多方面能力,时间持续了67.5个月,并使用中国的语言能力评估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学习成果。根据他们最新的研究结论,学习第二种外来文化的语言成功率会随着学生的年龄增加而降低。从而证明了二语学习关键期假说的成立。刘振前(2003)[5]对参加“二语习得关键期是否成立”的双方辩论理论进行认真研究,在综述了各方意见之后认为关键期假说理论依据不充分、不能成立。陈宝国、彭聃龄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可能有多种,每种语言成分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需要特别关注。[6]
5 研究成果概述与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二语习得关键假说的研究呈跨学科、多视角、多途径之势;研究范式有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多种范式。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传统心理学的语言行为实验与问卷调查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断层扫描(PET)、核磁功能成像(fMRI)等技术相结合,实现多维度技术手段共同参与。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迄今为止,缺乏足够的证据否定或肯定二语习得关键期的存在。对此,我考虑到有以下原因:
第一,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思想、情感、知识等多种功能的符号,与人类大脑神经机制密切相关,语言的形成机制异常复杂;
第二,非常接近的测试方法和手段得出结论却不一样,这并不是实验误差的问题也不是统计方法的问题,而是实验的被试是人,而人是有差异的,导致不同研究范式下的被试选择标准不够统一;
第三,测试过程中还受到被试社会环境、情绪、动机以及测试内容与被试认知风格是否匹配等众多因素的干扰导致研究中对某些变量控制随意性太大;
第四,对关键期概念相关的参数变量量规选择没有合理规范,如二语习得年龄、二语语言水平、本族语水平、二语及母语习得环境、二语习得动机、二语习得态度等;
6 研究方向新探索
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我认为需要寻求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策略,重点关注人类语言形成机制深层次的微观系统来探究答案,即语言形成机制与人脑密不可分。
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威尔尼克区(wernicke)在左颞叶,布洛卡区(broca)在左额叶,弓状束(arcuate fasciculus)是一串连接威尔尼克区和布洛卡区的纤维,还有角回(angular gyrus)都与语言功能密切相关,大脑语言功能区复杂的神经网络回路共同协作构建出语言形成的脑机制。[7]为了弄清楚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必须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脑的语言功能区域的神经系统,必须明白在语言习得的关键期,脑内的神经组织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如何与外部环境刺激相互作用。比如人类在1岁以内,突触的形成数量呈爆发趋势;到了成年的时候,所拥有的神经元细胞总数将降到出生时的一半左右,没有被激活的突触被修剪。神经髓鞘化使得信息传输速度加快,这是否影响神经元之间横向的互动?这些现象的发生是巧合的,还是人类必然的?这些现象对二语习得是正相关还是副相关?如何从众多的参变量中提取并测量代表人类语言能力的参数?又如青春期之后人类大脑的偏侧化现象动因是什么,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刺激因素,是否真正影响高效率地习得二语?这些都依赖于脑神经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回答。有了微观系统数据,再结合60多年积累的宏观数据,二者进行有效比对,就能极大促进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这一世界难题的破解。
7 结语
人类语言形成机制异常复杂,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神经语言学、语言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众多专家学者在各自视角对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都提出不同看法,研究方法推陈出新,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历经跨世纪不懈努力,提纲挈领,拨云见日,相信真理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参考文献:
[1] 周宗奎.儿童青少年发展心理学[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钟启泉.印刻现象与印刻研究[J].心理科学通讯,1985,(05)..
[3] 刘冬梅,高全.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 柴省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假设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05):692-706+799-800.
[5] 刘振前.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研究评述[J].当代语言学,2003,(02):158-172+190.
[6] 陈宝国,彭聃龄.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及其对教育的启示[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01):52-57.
[7] 彭聃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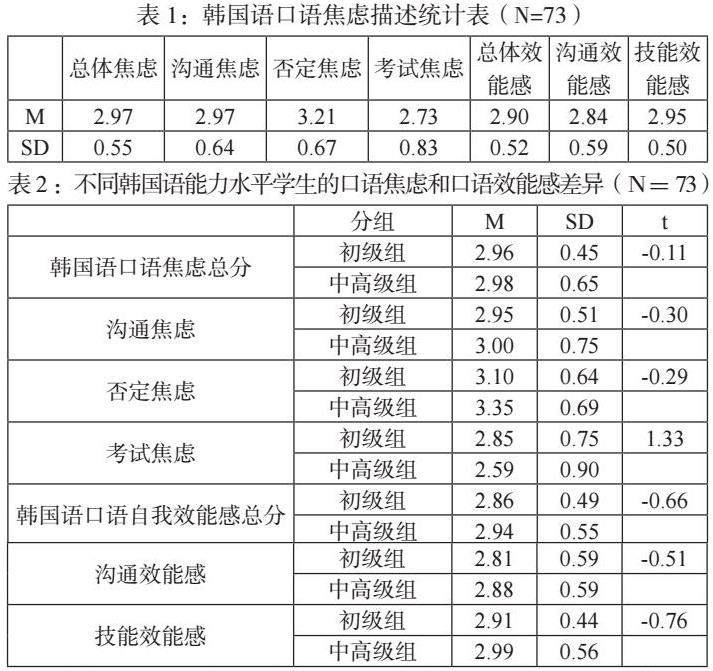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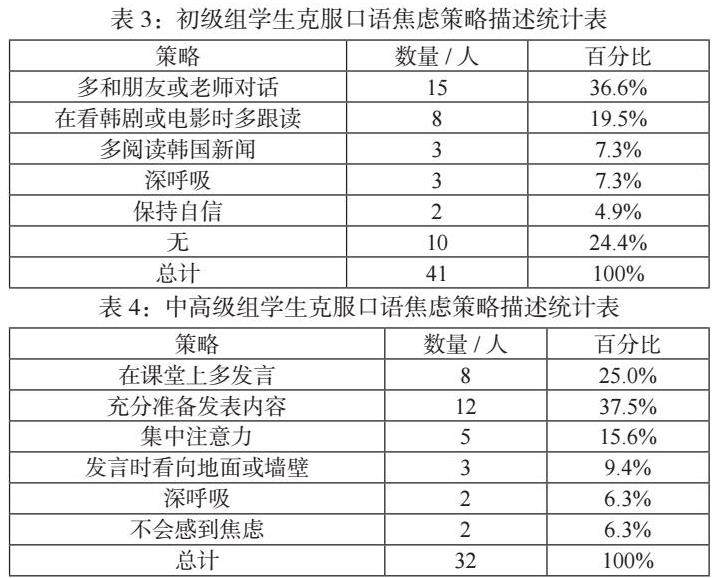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69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69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