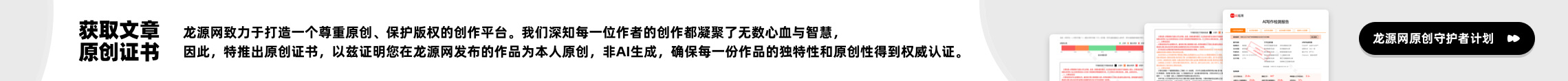
- 收藏
- 加入书签
浅析《米》中织云的人物形象
摘要:《米》是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红粉杀手”的苏童,他总能以其细腻、独到的手法书写对女性的认识。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浅析其中女性人物之一——“织云”的人物形象,以便思考作者的深层情感和作品背后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织云;大小姐;拜金;牺牲品;苏童
《米》是一个关于逃亡的故事。五龙从枫杨树乡村逃亡到城市里,在百般讨好冯老板之后成为了米店伙计。作为前期与五龙命运纠葛不清的米店里二小姐织云,是作者极力刻画书写的女性人物之一。织云从单纯善良的少女,经历了被玩弄、背叛、抛弃种种不幸后,变为大火之中悄然消散的尘埃,她最终没有逃开宿命的安排。在作者笔下,织云表现出非同寻常、个性鲜明的人物特征,下面将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形象:
一、“高人一等”的大小姐
“织云和绮云是瓦匠街著名的米店姐妹”,织云,从社会地位上来看,是大鸿记米店的大小姐。本身这个身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就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背景来看,米店成为了居民心中的天堂。当时兵荒马乱,到处灾荒,在“枫杨树乡村”系列小说中,“枫杨树乡”是贫困、饥荒、落败的代名词,那里的人们,从“茫茫的大水淹没了五百里稻田和村庄,水流从各方涌来,摧毁每一所灰泥房舍和树木”的枫杨树故乡而来,他们最渴求的仅仅是先满足人生存的基本欲望:对食物的渴望。于是包括五龙在内的流民都对米店,一个有很多粮食与钱财的地方,充满着虔诚的向往之情,将那里视作是梦想的港湾、理想的世界。在这样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织云米店大小姐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后来依靠攀附六爷,织云有了更多资本,华美的服饰和背后的势力,使她自认为逃离了米店,跳出了瓦匠街的世界,进入到更上流的圈子。“高人一等”是她自以为是的想法,她瞧不起瓦匠街上的所有人,甚至觉得自己的妹妹绮云也对她充满嫉妒艳羡。她将“跳到六爷的膝上”视作是荣誉和骄傲,将自己被说成和五龙是一对视作是笑话。因为深藏在她心底的是强烈的阶级等级观念。虽然她偶尔表现出善良的、大方的姿态,她可怜五龙,让五龙吃饱饭、给他买鞋,但这些行为基于将自身放置在更高社会地位之上,看似不与人计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内心深处自以为高高在上的想法和“不屑”的心理。
这些都丰富了她“大小姐”这一形象特征的内涵。
二、拜金主义者
拜金主义是把金钱视为具有魔法或法力无边的神予以崇拜的观念和思想体系。拜金主义者常认为金钱货币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下面将从两个方面具体分析织云拜金主义者这一形象特征的原因:
(一)迷恋物质满足和地位
她重视外在的物质满足,喜欢漂亮时髦的衣物,“我要一件水貂皮的大衣”是年仅十五岁时的她最迫切的渴望,而六爷满足了她的愿望,她便爱上了这个拥有财富、权势和地位的男人。但织云喜欢六爷,喜欢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人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纸醉金迷的气氛使她深深陶醉”,作者极力刻画了她爱慕虚荣、不满现状的性格特点。她在阳光下“满意自得”晾晒端详自己的衣物,在被拖曳时担心的是“我的裙子磨坏了”,回到娘家也不忘偷走绮云的翡翠镯子,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描写让我们看到她对物质的痴迷,虚荣、好面、自私的形象也随之生动化、具体化。
(二)金钱至上的价值标准
织云对金钱和地位的迷恋,促使她在人生选择上常坚持“金钱至上”的原则。她在面对因为一船米而失去的一条人命时,选择了满不在乎,因为同冯老板、绮云等人一样,他们的眼里只有金钱、利益;在有钱有势的六爷面前,权势左右了她的判断,驱使她迅速沉沦,甘心被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在被无情抛弃、羞辱后,她仍毫不犹豫地抓住做姨太太的机会,迅速地将自己的自尊抛之脑后,忘记所有的耻辱,即便是没有花轿,也要缠住六爷。从这些选择中我们能够看出:作为“拜金主义者”的织云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看问题的角度过于单一和片面化,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重大人生选择,她总屈服于财富、地位、命运、这种性格缺陷与其最终的悲剧宿命息息相关。
三、具有反抗精神的牺牲品
(一)放浪形骸
与传统观念中的妇女形象不同,织云并不乖巧、懂事、坚守节操和贞洁,她是“一朵妩媚的野花”,“美貌丰腴骚劲十足”。和多数人对爱情纯洁、忠贞的理解不同,她十五岁结识六爷,迅速成为了他的骈头。后又与阿保通奸、挑逗五龙、勾搭男人。不只是在当时,即便是在现代,她的行为都显得有些过于放荡。
她的亲姐妹绮云,两人性格上的不同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绮云所代表的一类人坚守封建思想文化道德,保守、刻板、循规遵矩,对织云这种超乎“常理”之外的行为表现出唾弃、厌恶的态度。两姐妹在血缘上是亲人,但由于思想、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尤其是在爱情观方面的不同,两人常常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她们更像两只充满敌意的猫,在任何时候都摆出对峙的姿态,亮出各自尖利的爪子”。对于绮云而言,织云是“丧门星”“一条不要脸的母狗”,因为她将“守身如玉”“忠贞如一”视作是女子应当坚守的职责和本分,而织云打破了这种传统,于是导致了灾祸。冰冷的仇恨横隔在姐妹之间,这里其实隐喻了封建卫道者与宣扬个性解放者之间的关系:二者存在巨大的认识差异和难以逾越的鸿沟,始终处于一种敌对、紧张、纠葛的矛盾状态。
织云的与众不同还体现在:她哼着轻佻粗俗而充满性的挑逗的小调,五花八门的脏话张口就来,阿保死后,她仍一如既往的放纵和快乐,丝毫没有改变她生活的内容和情趣。她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受世俗礼节的约束,可以说,织云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个怪诞、反常的“异物”。
(二)思想独立、充满反抗精神
织云有个人的主观意识,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象征。她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和想法,她并不十分关心米店的生意,“对这类事缺乏耐心和兴趣”,而是热衷于游走在各种社交场合。看似不慕名利,实际上是由于她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她不愿拘泥于“米店”这个小世界,而是向往更大、更自由的、外面的世界。
她叛逆、大胆、张狂,追求刺激的欲望,她说“这世道也怪,就兴男人玩女人,女人就不能玩男人”,“老娘就要造这个反”,她用世人不解的行为来反抗传统的三纲五常,这是深入这个人物背后所发现的更值得探究的奥秘。
苏童评:“《金瓶梅》的价值,突破禁忌是一方面,一些掩盖着的东西脱颖而出,大家觉得它显著的特点是性的描写,其实也可以是张扬了女性意识,尤其是性方面的自由主义”[1],织云这个人物,便可以被看作是突破禁忌的一次试炼。她想尽办法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放肆、自由,她身上具有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和反抗精神,她“玩男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另一个目的——对家长们恪守的封建秩序封建伦理由怀疑而反抗的文化手段。”[2]苏童通过这样的书写,不仅揭示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长期处于劣势、在男权社会中夹缝生存的历史现实,同时传达了自身对女性个体解放的独特思考,对自然人性的真诚人性的向往和追求。
(三)不彻底的反抗
织云身上具有的反抗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根本上说,她的反抗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反抗。以六爷为代表的男权文化将金鱼和女人相等同,认为二者都是腻了、不喜欢了就可以扔掉的玩物,而织云痛恨这种观念。她恨男人们,便用看似浪荡、自我作贱的行为来实施对他们的报复。她被六爷抛弃后,“迅速勾搭上一个男人”,因为她相信“没有他老娘照样可以寻欢作乐”,她也会有意无意的“勾引”男人,织云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以男人为主导思想的反对与抗争。
但真正到抉择的时候,织云又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向权势低头。“男人家的事女人家哪儿管得了”,自她回到吕家公馆,忍受下人的待遇自己洗衣、期待通过等待抱玉长大来改变命运时,就宣告了她抗争的彻底失败。这是这个小人物身上最大的悲哀,也注定了她悲剧性的命运走向。她最终成了与男权文化抗争的牺牲品。
织云的悲剧命运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自身存在的自以为是、自我放纵、虚荣拜金等性格缺陷,奠定了她一生命运坎坷、备受凌辱的悲剧基调。另一方面是来自他人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压迫与残害。有以绮云和冯老板等人为代表的原生家庭的嘲弄和讽刺,有来自五龙等变态心理下的折磨和损害,有来自以六爷为代表的男权力量的打压和毁灭,多种力量不断摧残、破环织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完整性,使这朵妩媚的野花最终残损、凋零。
结语
通过分析织云的形象,我们看到了织云作为大小姐,作为拜金主义者,以及作为牺牲品等多方面的形象特征。而在分析人物自身特性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到男权社会主导下女子的奋力反抗和挣扎却难逃宿命的悲剧现实。这对引起人们对女性命运的思考,探寻“无论如何背离现实和历史,女性似乎永远无法逃脱属于女人的命运和性别悲剧”[3]这样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性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也是简要分析人物更重要的意义和原因所在。
苏童作为一名男性作家,用他更为客观、冷酷、犀利的写作视角,超越多数男性作家对女性心理的把握,甚至胜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理解,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冷静与犀利”[4]进行了文学上一次很难得的尝试和探索,为此后更好书写女性主题提供了经验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苏童,王宏图. 南方的诗学:苏童、王宏图对谈录[M].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2.
[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7
[3]吴雪丽,苏童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8,55
[4]刘文辉,邵维加,“中性”叙事姿态下的机遇与困境 ——论苏童小说女性形象的塑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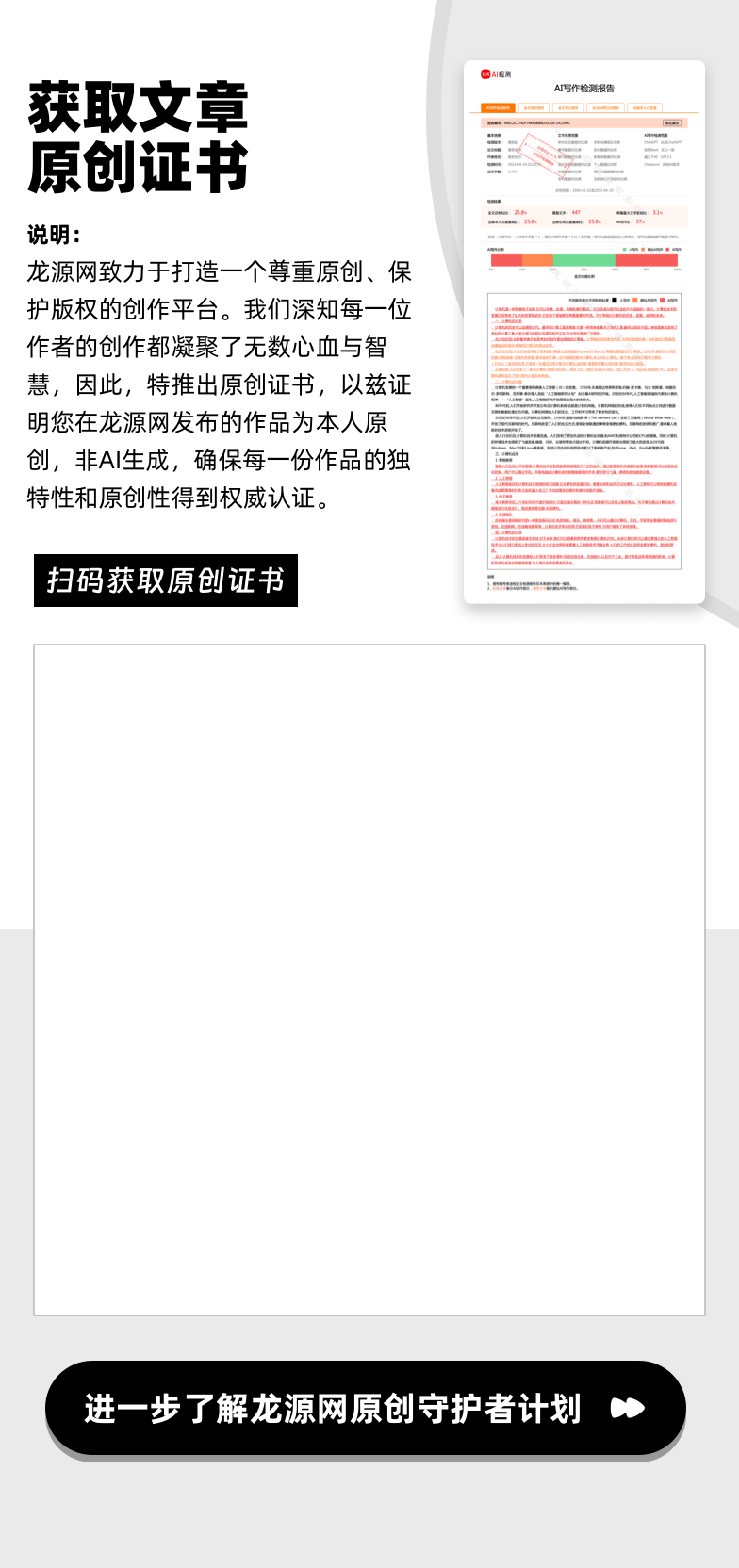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69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3690号


